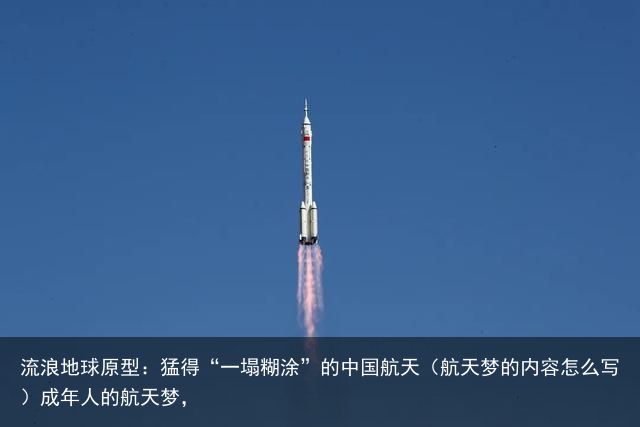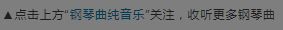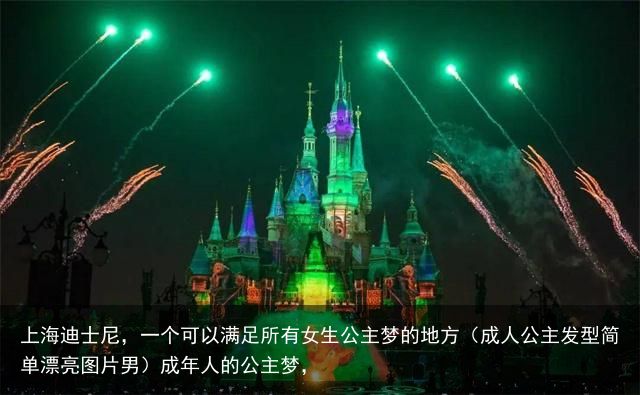一个单身男人的白日梦(白日梦tears钢琴曲)成年人的白日梦钢琴曲,
单身男人的白日梦
世上最浪漫的人无疑是那些无人与之浪漫的人。
正是在我们身处孤独、没有工作或朋友来干扰内心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爱情的精髓和必要性。整整一周时间电话寂静无声,每顿饭都是罐装食品,一边吃一边听着BBC播音员沙哑的毫无慰藉作用的声音——这个声音在描绘肯尼亚羚羊的交配习惯——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柏拉图曾声称没有爱的男人,就像一只仅有一半躯体的动物。
在这种遗世独立的时刻出现的白日梦很难说得上成熟,如果我们认为成熟意味着我们明了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危害的话。
在前往爱丁堡的一列火车上,我的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士,读着公司简报样的东西,一路吮吸着一盒苹果汁。当我们一路向北飞驰时,我假装在欣赏窗外的风景(干枯的田野和工业废墟),实际上却被眼前的天使牢牢吸引。
栗色短发、苍白的皮肤、灰蓝色眼睛、鼻子上一簇雀斑,身穿条纹水手上衣,上面有一块小而明显的污渍,可能是午饭时吃通心粉留下的。列车过了曼彻斯特,朱丽叶放下手中的公司简报,拿起一本菜谱。《中东食品》。眉头透露出她很专注。夹心茄子。还有炸豆泥三明治、塔博勒色拉和古鲁可模样的东西,需要放入很多菠菜。她不时记下要点,笔迹弯弯曲曲的,但颇为认真。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陷入对一个人的爱真是太容易了。或者至少可以说陷入一种对另一个人的强烈的激情真是太容易了,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称其为爱、迷恋、病态或幻觉。当列车经过纽卡斯尔的时候,我已经在想和她结婚,在长满樱桃树的道路旁有我们的屋子,周日晚上她躺在我身边,我用手指梳理她栗色的头发,我们会静静地享受她做的某种中东饭菜,然后我终于感觉自己在这个世上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为之满怀感激之情。
类似时刻点缀着单身男人的生活,在前往爱丁堡的列车上、吃三明治午餐的时候或在机场大厅,可能只是惊鸿一瞥,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而没有丝毫外在行动表现出来。真是哀婉动人的故事,但毫无疑问,对夫妻生活极为重要。
女士们应该感谢单身男人的绝望,因为正是这种绝望构成了未来坚贞不渝、无私奉献的坚实基础——或许还因为,这些在浪漫生活方面极为成功的人应该受到质疑,他们应该是缺乏相应的魅力,都没来得及经历好几天思慕一个女人的悲喜过程,他们由于害羞而不敢跟一个女人打招呼,而这个女人却在下一站下了车,留给男人的只是一个空的苹果汁盒与一箩筐的结婚计划。
成人参观动物园的启迪
如果你去动物园参观,却不带小孩,人们会以奇怪的眼神看你。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带着一群小孩,并让他们吃着滴滴答答的冰激凌,手里还拿着一些气球。
参观一个有东方小爪水獭或豹斑壁虎的动物园,似乎并非一个成年人度过下午的理想方式。当前伦敦的时髦话题是,你是否参观了国家美术馆举行的安格尔画展,而不是摄政王公园里的伦敦动物园新来的倭河马。
但我5岁的侄子在最后一刻爽约(他突然想起当天是他最好朋友的生日),而我固执地决定按照原定计划度过这个下午。我的第一个想法——在我买了冰激凌之后,虽然我没有买气球——是动物看起来多么奇怪。
除了奇怪的猫、狗或马,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过一只真正的动物,一只长相奇特、熟悉丛林法则的生物。拿骆驼为例:一个U形脖子、两个毛茸茸的驼峰、像涂着睫毛膏似的眼睑以及一口黄色龅牙。旁边有介绍资料:骆驼可以在沙漠行走10天,而无须喝水;它们的驼峰里装的不是水,而是脂肪;它们的眼睑如此设计是为了阻挡沙尘;它们的肝脏和肾脏能够从食物中吸干所有水分,使得它们的粪便又干又硬。
介绍中还说,它们是世界上适应性最强的动物之一——对此我不由产生出一种幼稚的嫉妒,感叹人类的肝脏和肾脏有所不及,惋惜我们没有毛茸茸的驼峰,不然的话,可以让我们免去下午的茶点。

如果动物们如今看起来如此奇怪,那是它们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达尔文如是说,身处摄政王公园,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斯里兰卡的懒熊长着长长的灵活的嘴唇,缺少两颗上门牙,这样它就可以从蚁窝里舔舐蚂蚁和白蚁,任何一个从熟食店里买午餐吃的人对这种独具特色的面部特征都会很困惑。
我一边吃着冰激凌,一边看着在烂泥中打滚的像涂了焦油似的倭河马,不由悲从中来。“恐龙”一词浮现在我的心头,并非它们与恐龙相像,而是因为它们让人想起恐龙是极端缓慢地适应环境的代名词。它们在世界上已经为数不多,未来的非洲大自然,将是更加灵活、更喜欢交配、如同小羚羊一般的动物的栖息地。
参观动物园,可以证明一句老生常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每一个动物似乎都完美地适应某些事物,却与其他类型的事物势不两立。马蹄蟹永远不会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它看起来就像一个长着弯腿的缩小版的军用钢盔),也不会阅读吉本,但它却是深水生存的明星,从而不被鲨鱼吃掉。它安静地生活,偶尔在大洋底部滑动,去捕食软体动物。
当我们被迫参加饭后的“如果你必须成为一个动物,你想成为什么”游戏时(很可惜,这个作为晚上娱乐的游戏逐渐被看图猜词所代替),我们难免认同一些动物,而抨击另一些动物,只要能够叫得出名字。福楼拜喜欢这个游戏;在他的信中,他把自己比作不同的动物,如大蟒蛇(1841)、贝壳中的牡蛎(1845)、缩成一团来保护自己的豪猪(1853、1857)。而我则把自己比作马来貘、小霍加、美洲鸵和乌龟(特别在周日晚上)。

动物园一边使动物看起来像人,一边使人看起来像动物,故而让人内心不安。
“猿猴是人类的近亲,”猩猩笼子旁的图片说明文字里介绍说,“你能够发现多少相似点?”相似点当然太多了,超出了我们能够接受的程度。给它刮刮脸,穿上T恤和运动裤,那么坐在笼子一角挠着鼻子的那位就是我的表兄,只不过乔在白赛姿公园有一套大公寓房,而且这个夏天和他的孩子们在多塞特郡度过了两周的时光。
1842年5月,维多利亚女王参观了摄政王公园里的伦敦动物园,她在日记里谈及一只刚刚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猩猩:“他很棒,喝茶时自斟自饮,他虽然像人,却让人感到痛苦和难受。”(读到这里,我想象自己被抓住后,关在假日旅馆房间那样的笼子里,通过一个小门传送一日三餐,一天无所事事,只能看电视——旁边有一群长颈鹿前来参观我,喜笑颜开,拍照摄影,舔着冰激凌,说我的脖子多么短小。)
我走出动物园,手里拿着一个德斯蒙德·莫利斯望远镜,这或许是难以避免的事情。打电话约莎拉一起吃饭有其特定目的,它只是人类求偶仪式的一部分,与秋日晚上美洲鸵开始朝彼此怪叫并无本质差异。
一个人的怪异行为从本质而言往往是简单的动物性目的——食品、居住和后代的繁衍——的复杂化体现,如果能够发现这点,人们将再次获得一丝安慰。我或许应该去申请一张摄政王公园里的伦敦动物园的年票。
写作如何再现生活
8岁时我写了第一本书。这是我的暑假日记,我和父母、姐姐和狗一起在法国乌尔加特的诺曼底海滨胜地度过了这个暑假。“昨天没有事情发生。今天天气很好。我们整天游泳。我们午饭吃了色拉。我们晚饭吃了鲑鱼。晚饭后我们看了电影,讲一个人在秘鲁发现了金子。”
这是很典型的一篇,标着1978年8月23日,星其三(其中的用词错误并非语言障碍,而是拼写水平还不行)。如果这本书难以卒读,那是因为它尽管初衷良好、书写整齐,但作者似乎并不能传达真正发生的事情。虽然提供了一系列事实,诸如鲑鱼和天气报道,但真正的生活却似乎没有显现出来。就如同观看家庭录像,却只能看到脚或云彩,你会困惑不解,很想知道在人们的脸部正在发生什么。

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即使拼写水平提高了,也必须经历一个痛苦的组织语言的过程,才能够真正实现我们的表达目的。典型的情况是,文字描述仅仅在事物的表面滑过,我们看到一次日落,然后在写日记时搜肠刮肚,将其称为“漂亮”,我们深知还有很多东西尚未表达,却无法将其用语言呈现,然后很快被抛之脑后。我们为了描述今天发生的一切,列下一个清单,记录我们去过哪里,看过什么,但离开纸页的时候,心里明白有一些转瞬即逝的事物我们没有呈现出来,而我们怀疑,或许正是这些事物才是解开今天真实情况的钥匙。
呈现真实的生活,难于对感官体验的忠实记录。将看到的事物进行记录,并不足以成为艺术:只有经过筛检、选择和思考的过程,笔下的事物才有可能显得真实。以下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中记录下的1915年2月15日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今天下午伦纳德(丈夫)和我都去了伦敦;伦去了图书馆,我则漫步伦敦西区,顺便购买一些衣服。我的确衣衫褴褛。随着年龄的增长,让我不再惧怕装饰华丽的商店。我逛遍了德本汉姆百货公司和马歇尔斯百货公司。然后喝了一杯茶,一路走到公园里的查令十字街,心里构思着词语和事件,以便写作。或许,就是一个人死亡的方式。我买了一件10英镑11便士的蓝色裙子,就是我此时此刻身上穿着的这件。
很难具体说清楚为什么这样写就可以,为什么在这样的描述中生活没有被剥离。好像伍尔夫只是选择了合适的细节,她知道应该看什么;或许是关于装饰华丽的商店的坦白中包含有什么,或许是她有能力意识到查令十字街上的自己行为的怪异,或许是“我此时此刻身上穿着”传达出了一种亲密。

他人之书的悖论在于,它们能够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远甚于我们对自己独自的理解。他人书本上的文字,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我们是谁,我们的世界如何。比如说,是歌德的年轻人维特让我明白年轻和单相思意味着什么,是福楼拜的药剂师赫麦让我从政治家或广告商身上看到博学的愚蠢,是普鲁斯特的一些痛苦的文字让我理解了我妒火中烧时的面目。
但伟大书籍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描述与我们生活中相似的感情和人物;它的价值还在于能够以比我们更加完美的方式描述这些感情和人物,它能够提供一些感受,我们虽然能明确认识到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感知,但却无法自己将其表达出来。
比如,我们或许已经认识某人,酷似普鲁斯特笔下的虚构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我们或许已经感觉到这个女人身上有些盛气凌人、傲慢无礼的地方,却并不清楚到底在哪里,直到普鲁斯特仔细地在括弧里描绘了公爵夫人对他人的反应,公爵夫人又叫奥利安·德·劳美,在一个时髦的宴会上,德·加拉尔东夫人喊了公爵夫人的名字,因显得与公爵夫人过于熟悉而犯了错误。
“奥利安”(立刻,劳美夫人又好笑又惊讶地转过头,面向一个隐形的第三者,她似乎要让其证明,她从来没有赋予加拉尔东夫人喊自己名字的权利)……
如果一本书关注这种细微、关键、令人震颤的时刻,一旦我们放下书本,继续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事情,将恰好是那些作者在相同情况下面临的事情。我们的思维就像最新调试的雷达一样,能够找到浮现在意识表面的特定事物,这种效果就如同把收音机拿进房间,我们本以为房间里安静无声,却发现安静仅仅存在于特定的频率,事实上,和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的,有来自乌克兰广播电台或小型出租车公司夜间呼叫的声音电波。我们的视线会被引向天空多彩的颜色、人脸多变的表情、虚伪多变的朋友,或某种隐藏的关于某种情形的悲伤情绪,我们此前根本不知道我们居然会为此而伤心。

本文节选自

《无聊的魅力》
作者: [英] 阿兰·德波顿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副标题: 阿兰·德波顿文集
原作名: On Seeing and Noticing
译者: 陈广兴
出版年: 2013-10-1
编辑 | 芬尼根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布莱克书店》豆瓣剧照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