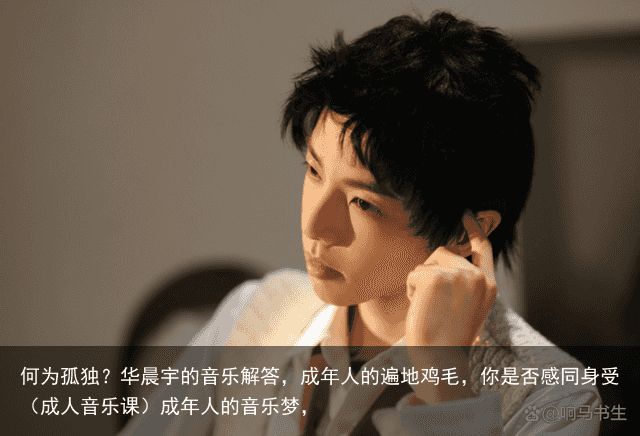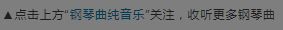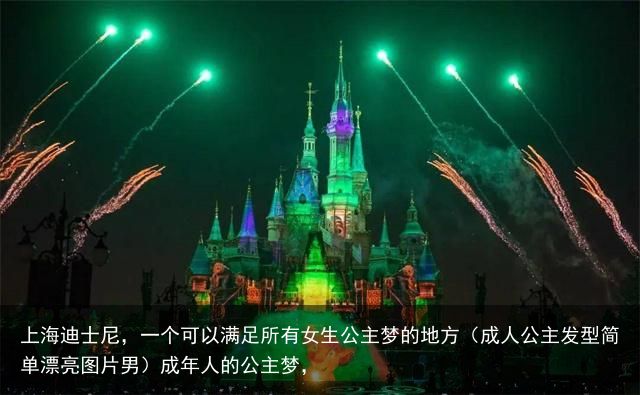弗洛伊德:作家创作与做白日梦的关系(白日做的梦会实现吗)成年人做的白日梦,
我们这些外行总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要知道,作家从什么源头汲取了他的素材,他如何用这些素材才使我们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才在我们心中激起了我们也许连想都没想到自己会有的情感。如果我们向作家请教,他本人也说不出所以然,也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正是这个事实引起了我们更大的兴趣;即使我们彻底地了解了作家是怎样决定选材的,了解了具有创造性想象力的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所了解的一切也根本不能帮助我们自己成为作家,——尽管如此,我们的兴趣一点儿也不会减弱。
如果我们能够至少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在像我们一样的人们身上,发现在某些地方有与创作相类似的活动该多好啊。检验这种活动将使我们有希望对作家的作品开始作出一种解释。确实,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毕竟作家自己是喜欢缩小他们这种人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的;他们一再要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心灵上都是一个诗人,不到最后一个人死掉,最后一个诗人是不会消逝的。
01 孩子的游戏世界 = 成年人白日梦?
难道我们不该在童年时代寻找想象活动的最初踪迹吗?孩子最喜爱、最热衷的是玩耍和游戏。难道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孩子在玩耍时,行为就像是一个作家吗?相似之处在于,在玩耍时,他创造出一个自己的世界,或者说他用使他快乐的新方法重新安排他那个世界的事物。如果认为他并不认真对待那个世界,那就错了;相反,他在玩耍时非常认真,并且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与玩耍相对的并非是严肃,而是真实。尽管孩子满腔热情地沉浸于游戏的世界,他还是相当清楚地把游戏的世界与现实区别开来;他喜欢把想象中的事物和情景与真实世界中可能的和可见的事物联系起来。这个联系就是使孩子的“玩耍”不同于“幻想”的地方。
作家的所作所为与玩耍中的孩子的作为一样。 他创造出一个他十分严肃地对待的幻想的世界——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幻想的世界怀着极大的热情——同时又把它同现实严格地区分开来。但是,作家想象中世界的非真实性,对他的艺术方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后果;因为有许多事情,假如它们是真实的,就不能产生乐趣,在虚构的戏剧中却能够产生乐趣。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本身实际上是令人悲痛的,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上演时,它们却能变成听众和观众的快感的源泉。
当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再不做游戏时,在他工作了几十年后,以相当严肃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之时,有一天他可能会发现他自己处于再次消除了戏剧与现实之间的差别的精神状态之中。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能够回顾他曾经在童年时代做游戏时怀有的热切、认真的态度,并且把今天显然严肃的工作与童年时代的游戏等同起来,靠这种方法,他可以抛弃生活强加在他身上的过分沉重的负担,获得幽默提供的大量的快乐。
于是,当人们长大以后,他们停止了游戏,他们好像也放弃了从游戏中获得的快乐。但是无论谁,只要他了解人类的心理,他就会知道,让一个人放弃他曾经体验过的快乐几乎比任何事情都困难。事实上,我们从来不可能丢弃任何事情,我们只不过把一件事情转换成另一件罢了。似乎是抛弃了的东西实际上被换上了一个代替物或代用品。同样,长大了的孩子在他停止游戏时,他只是抛弃了与真实事物的联系,他现在用幻想来代替游戏。他在空中建筑城堡,创造出叫作白日梦的东西来。我相信大多数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是不时地创造着幻想的。这是一个长时期被忽视的事实,因此它的重要性就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人们的幻想比儿童的游戏难于观察。的确,一个孩子独自游戏,或者为了游戏与其他孩子组成一个紧密的精神上的组织;尽管他可能不在大人面前做游戏,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并不在大人面前掩饰自己的游戏。相反,成年人却为自己的幻想害臊,并在别人面前把它们隐藏起来。他把他的幻想当作最秘密的私有财产珍藏起来,通常,他宁可坦白自己的过失也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幻想。因此,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他相信唯有他创造了这样的幻想,而不知道在其他人那里这类创造十分普通。游戏者和幻想者在行为上的不同是由于这两种活动的动机不同,然而这两种活动的动机却是互相依附的。
孩子的游戏是由愿望决定的:事实上是唯一的一个愿望——它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起很大作用——希望长大成人。他总是装扮成“成年人”,在游戏时,他模仿他所知道的比他年长的人的生活。他没有理由掩饰这个愿望。成年人的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他知道他不应该再继续游戏和幻想,而应该在真实世界中行动,另一方面他认为把引起他幻想的一些愿望隐藏起来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他便为他那些孩子气的和不被容许的幻想而感到羞耻了。
但是,你会问,如果人们把他们的幻想弄得这么神秘,我们对这件事情又怎么会知道得那么多呢?是这样,人类中有这么一类人,被严厉地要求让他们讲述他们遭受了什么痛苦,以及什么东西给他们带来了幸福。他们是精神病的受害者,他们必须把他们的幻想夹杂在其他事情中间告诉医生,他们希望医生用精神疗法治好他们的病。这是我们的知识的最好来源,因此我们找到了很好的理由来假设,病人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从健康人那里也能听到。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幻想的几个特征。我们可以肯定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幻想,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作为动力的愿望根据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不同而各异,但是它们天然地分成两大类。它们,或者是野心的愿望——用来抬高幻想者的个人地位,或者是性的愿望。在年轻女人的身上,性的愿望占有几乎排除其他愿望的优势,因为她们的野心一般都被性欲的倾向所同化。在年轻男人身上,自私的、野心的愿望与性的愿望共存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但是,我们并不打算强调两种倾向之间的对立,我们最好是强调它们经常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事实。
关于幻想还可以讲许许多多,但我只是尽可能简明地说明某几点。如果幻想变得过于丰富,过于强烈,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发作的条件就成熟了。而且,幻想是我们的病人抱怨的苦恼症状的直接心理预兆。这里,一条宽阔的岔道进入了病理学。
02 作家的创作像白日梦,是童年游戏的继续和代替物
关于幻想就谈这些。现在来谈谈作家。我们真能够试图将富于想象力的作家和“光天化日之下的梦幻者”进行比较吗?将他的创作和白日梦进行比较吗?这里,我们必须从做最初的区别开始。我们必须区分开这两类作家:像古代的史诗作家和悲剧作家一样接受现成题材的作家,似乎是由自己选择题材创作的作家。我们将要谈的是后一种,并且为了进行比较,我们将不选择那些批评家们最为推崇的作家,而选择那些评价不高的长篇小说、传奇文学和短篇小说的作者,他们拥有最广泛、最热忱的男女读者群。
首先,这些小说作者的作品中有一个特征不能不打动我们: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主角作为兴趣的中心,作家试图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他赢得我们的同情,作者似乎把他置于一个特殊的神的保护之下。如果在我的故事的某一章的结尾,我让主角严重受伤,流血不止,失去知觉,我肯定会在下一章的开始让他受到精心的护理,并逐渐恢复起来。如果第一卷以他们乘的船遇到暴风雨沉没为结尾,我们可以肯定,在第二卷一开始就会看到他奇迹般地获救——没有这个情节,故事将无法进行下去。我带着安全感跟随主角经历他那危险的历程,这种安全感就像现实生活中一个英雄跳进水里去救一个溺水者,或者为了对敌人猛烈攻击而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的感觉。这是真正英雄的感觉。我们的一个最优秀的作家用一句无与伦比的话表达了这种感觉:“我不会出事情的!”但是,在我看来,在这种从不受伤害的特性的启示下,我们可以立即认出“至高无上的自我”,就像每一场白日梦和每一个故事的主角一样。
《恋与制作人》,一款满足女性爱情幻想的游戏
这些自我中心的故事的其他典型特征指出了同样的类似的性质。小说中的所有女人总是爱上了主角,这一事实很难看作对现实的描写。但是,作为白日梦的必要成分,它却很容易被理解。同样,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严格地分成好人和坏人,无视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人类性格的多样性。“好人”都是自我的助手,“坏人”都是自我的敌人和对手,这个自我就变成了故事的主角。
凭着我们从研究幻想得来的知识,我们应该预期如下的事态:现时的强烈经验唤起了作家对早年经验(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验)的记忆,现在,从这个记忆中产生了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又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作品本身展示出两种成分:最近的诱发场合和旧时的记忆。你将不会忘记对作家生活中童年时代记忆的强调——这个强调也许是令人迷惑的——最终来自一个假设: 一篇创造性作品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时代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和代替物。
你一定还记得我在前面论述了白日梦者因为觉得他有理由为他的幻想感到害羞,便小心翼翼地在别人面前掩藏自己的幻想。现在我应该补充说,即使他把这些幻想告诉我们,他泄漏出来的东西也不会使我们感到快乐。当我们听到这些幻想时,我们会产生反感,至少是不感兴趣。 但是,当一个作家把他的戏剧奉献给我们,或者把我们认为是他个人的白日梦告诉我们时,我们就会感到极大的快乐,这个快乐可能由许多来源汇集而成。 作家如何完成这一任务,这是他内心深处的秘密; 诗歌艺术的诀窍在于一种克服我们心中的厌恶的技巧,这种厌恶感无疑跟单一“自我”与其他“自我”之间的隔阂有关。
我们可以猜测发挥这个技巧的两种方式: 其一,作家通过改变和伪装他的利己主义的白日梦以软化它们的性质;其二,在他表达他的幻想时,他向我们提供纯形式的——亦即美学的——快乐,以取悦于人。 我们给这类快乐起了个名字叫“前期快乐”(fore-pleasure)或“额外刺激”(incentive bonus)。向我们提供这种快乐是为了有可能从更深的精神源泉中释放出更大的快乐。我认为,一个作家提供给我们的所有美的快乐都具有这种“前期快乐”的性质,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给予我们的实际享受来自我们精神紧张的解除。甚至可能是这样: 这个效果的不小的一部分是由于作家使我们从作品中享受到我们自己的白日梦,而不必自我责备或感到羞愧。 这个问题将把我们引向另一些新的、饶有兴味的和复杂的调查研究,但是,在目前,这一点至少已经把我们带到了我们的讨论的终结。
本文节选自
《达·芬奇与白日梦》
作者: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副标题: 弗洛伊德论美
译者: 张唤民 陈伟奇
出版年: 2020-5-1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