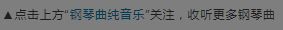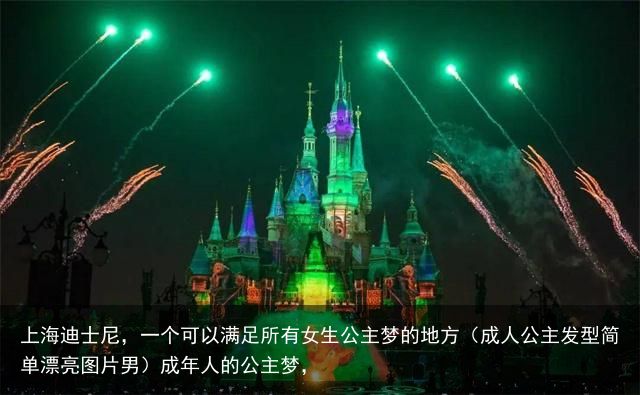“梦核/怪核”美学:粉红色的蜜糖梦境和指向未来的幽灵回声(大人梦想是什么)成年人的梦都是什么,
“这是你童年时期呆过的幼儿园。楼梯上去就是你睡午觉的地方。你要上去吗?你确定十多年过去,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还是你记忆里的那样吗?粉红色的墙,劣质宝石做成的时钟,彩色的流苏在电风扇下飘动,耳边仿佛是孩子们的叫声和笑声……”
“我在哪里?我能够去哪里?这是车站、走廊、两个目的地之间的阈限空间,改变和维持现状之间的临界状态。看见前方那个黑色的门了吗?它宛若黑洞吸收掉一切的光,摇曳的电灯泡只剩下昏暗……你决定开门走进去吗?你要登上下一班地铁吗?”
“轻松一夏,windows98:亲人的低像素照片被剪贴进迷幻的屏幕保护程序里,穿过数码迷宫通往你童年记忆深刻的无忧无虑的草坪、屋顶、远方的群山,直到你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张桌面壁纸,开始菜单,程序页面,你在屏幕里哭喊着要回家却叫不出声音……”
以上这些怀旧的,梦幻的,超现实主义的,带有阴郁恐怖色彩的视觉场景和沉浸式感受,是近两年来从Youtube萌发,迅速流行全世界,并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中以“中式恐怖”为突破口得以“本土化”的“梦核/怪核”(Dreamcore/Weirdcore)美学的具象化。以“梦核/怪核”为代表的“核类美学”,是一种超现实的迷幻视觉风格,是一种偏好低保真低像素的平面设计概念,是一类电子音乐的形式转译,却更是一种隐藏的图像式叙事,一种承接了“蒸汽波”的属于21世纪初的青年“怀旧”图景——当Y2K一代人尚未老去就开始追忆过去,就开始在赛博空间中思索死亡和存在,以粗粝模糊的“劣质”素材标榜内心的时候,一切都在灰暗的黑洞里随着潜意识不断下坠,“梦核”中虚无缥缈的粉红色梦境,也许正是为当代人与世界、与时代采取的疏离、封闭态度所刷上的一层蜜糖式的幽灵回声。
“核类美学”:超现实主义艺术的赛博世界复生
如若从美术史的眼光来看待“梦核/怪核”作品,我们不难指出它们都是20世纪上半叶萌芽的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当代复兴。布列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指出:“超现实主义,即精神的无意识行为,是一种通过口头、书面或其他任何形式进行思想表达的运作过程。它完全由思想决定,不受任何理性的约束,也不受限于任何审美或道德理念。”立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取向,超现实主义将人类心灵中“潜藏的冰山”潜意识作为一种更加“真实”的存在来描摹。无论是玛格丽特的苹果、烟斗、宫殿中的巨石和鬼魅的蓝天白云,达利融化的时钟和扭曲的蓝色眼睛,基里柯规整却诡异的长廊与心神不宁的缪斯,都可以被称为那个时代的“梦核/怪核”——那么,可以把20世纪初思想界与艺术界对于机器统治灵魂的虚无抗争,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的未来迷惘,置于21世纪初的当代大众心态进行互文:我们再次到了从潜意识和梦境中寻求慰藉的时刻。
当代互联网的“梦核/怪核”美学很难具体归类,它们往往是跨越式的,每一个作品都横跨在阈限空间的临界点上。“核”,原文“core”,法语的“心”,在英文中作为“核心”的意思,天然自带对个体性的、小众的怪诞艺术的特别专注,也因此带有排外性质,用以称呼“顽固或不屈不挠的少数群体”。“核”的概念最初用于小众的音乐风格,并逐渐通往以美术、文字、时尚和多媒体图像作品为载体的亚文化圈层。通常而言,直接从超现实主义发展而来的“怪核”(Weirdcore)被认为是这一类“核类美学”的鼻祖,一位叫做DavidCrypt的YouTuber在2010年第一次集中向网友介绍了“怪核”的概念。“怪核”视觉作品往往以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场景为素材,却以业余的、低品质的摄影技术为这些“熟悉”的画面蒙上一层陌生与距离感。这些低保真的图像素材,糟糕的排版,业余的处理技术,配上21世纪初的windows艺术字体背后所蕴含的“日常”和“大众”性,往往构建出一种严肃的,足以引发大规模共情的存在主义语境:“我在哪里?”“我将去往何方?”“这幅图里有哪些地方不对吗?”等诸如此类的文字,为不和谐、高对比度的画面做了更加直观的交互性注解——此时,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无不体验到某种迷失方向的怅然,不解和迷惑,以及在这种未知与不可控的迷雾中所衍生的恐惧;一种蓝天白云、光天化日之下的心灵恐惧。
而随着TikTok的“梦幻”特效带动的视觉风潮,“梦核”(Dreamcore)这种贴合21世纪初Y2K一代的私人美学取向的风格,在2020年前后以更加“无害”的面貌走进大众视野。围绕“梦境”,人们会有更加美好、空灵乃至遥远的想象,然而“梦”往往却也来自人们更加熟悉的生活与记忆。由此,对熟悉的过去和记忆进行“梦幻”的美化,这种粉红色的“怀旧”,连带着进一步提醒我们现今生活的虚无和梦境本身的遥不可及。“梦核”作品常与马戏团、幼儿园等“童年”元素绑定,低保真的元素被蒙上一层“雾气”,更加朦胧和晶莹剔透;人们在怀念纯真美好的童年时光的同时,更意识到这种怀念纯粹是“梦”,甚至连“美好童年”这一本体可能都是后发证成的虚假掩饰。由此,“梦核”在灿烂璀璨的皮相之下,更指向Y2K一代人根深蒂固的孤独心态:私人的回忆,对甜蜜时光的怀恋乃至幻想,对“可爱”与否的自我判断和对心理临界状态的甘之如饴,这些孤僻却又普遍的大众情绪,如果进一步撕下梦境甜美的外壳,则发展成为“核类美学”中更加直面内心暗面的范畴:“伤核”和“后室空间”。
“伤核”(Traumacore)顾名思义,与创作者所受到的心灵创伤密切相关。“伤核”作品从视觉上并非特别阴暗,其往往与“梦核”一脉相承,都以少女的视角来描绘童年时代的意象:儿童卧室,游乐场,幼儿园,HELLO KITTY等卡通形象,然而这些甜美的意象组合,同时也是诡异和超出现实逻辑的,在柔和的光线下带有“过分完美”的不安,有着“即将腐败”的预兆。在甜美精致的洛丽塔式封套下包裹腐烂、灰尘和死亡,是“伤核”作品惯用的手法,“苦乐相伴”(Bittersweet)是基本的情感基调,被虐待、被操控的精神苦难多以文字的形式来打破画面的完满,由此几乎任何美好天真的“童年”意象,都会被“伤核”的美学带向恐怖的,令人不堪回首的反面,也正是应激性的负面情绪输出,更显出受创伤者原有的天真无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核类美学”是一种创伤性的,受害者视角的美学表达,它的成品往往都具备治愈、满足和制造幻象的补偿性功能,而“补偿”在赛博世界的终归虚幻,也是一代青年人的心灵世界走向虚无和麻木的精神共性。
由此,以“后室空间”(Backroom)和“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为代表的,更与恐怖艺术和“都市传说”贴合的互联网美学创作,是“核类美学”中最阴暗深沉的部分。在心理学范畴中,来源于拉丁文中指地狱边缘的临界空间的“Limbo”,被解释为人类潜意识与现实交界的过渡空间,而“后室空间”和“阈限空间”的概念,就是指这种心理学或者神学范畴中的“心灵边界”空间在现实生活中的样貌。这些美学作品大量直观地展现如地铁站,楼房各房间之间的走廊,地下道,楼梯口等“边界”性质的幽闭无人空间,以“边界”作为隐喻桥梁,辅以“怪核”美学一贯的低保真、粗糙的视觉处理,再加上与“都市怪谈”密切结合的恐怖氛围的音效、视觉扭曲和运镜,达成将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过渡性”场景提升到心灵的“边界”和“选择区域”,指向存在主义的自我思考:我是谁?我为什么不属于任何一个领域?我为什么要做出选择?我的选择会让我通向哪里?我们的肉体身处“阈限空间”,正是潜意识被尘封进“Limbo”的互文呼应,在“核类美学”的渲染下,我们每日的普通生活,都实际上是心灵在寻找真正的归属地的奥德赛流亡冒险;然而在大多数当代创作者看来,这种冒险的终点不可能是圆满的,我们必然走不出“Limbo”,必然沉溺于永恒轮回,必然被恐怖的不可名状的未知所攫取甚至消灭,从而被记录为深夜惊魂的“都市怪谈”。
归属感。当我们试图归类近乎不可归类的“核类美学”时,我们能够把握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我们难以把握自己这一事实。20世纪初的超现实主义者无限的拼贴、组合和“陌生化”的惊奇,是为了突破现实世界的陈腐僵化;而立足于现实世界的,对过往梦幻的记忆复兴的“梦核/怪核”,则更多是在对至少在梦境里存在过的,“真实”过的美好现实世界做“流水落花春去也”式的悼亡,当美好的记忆都化作赛博空间里虚妄的低保真图像,当我们都被限制在“阈限空间”里找不到现实和心灵的双重出口,这种以超现实主义传统为基底,却根本上是从赛博世界自发涌现出来的“亚文化美学”,其实本质蕴含的,是最为切实的,植根于大众内心深处的,最为普遍的当代现实主义:在20世纪初和21世纪初之间的一百年里,我们仿佛有一个真正美好的、足以被称作梦境的世界,虽然身处其中的人从来未曾察觉,但已足以令下一代人在“阈限空间”里乐不思蜀,对“梦核”画面中刷上的一层蜜制糖霜魂牵梦萦。
流溢的非作品性:赛博世界的美学新存在形式
行文至此,我们对“核类美学”的分析似乎缺乏艺术哲学的本体论:具体的作品在哪里?我们谈论的美学现象早已覆盖全世界的互联网,相关的视频点击以亿万计数,在网络视频制作、电子音乐MV、时尚设计、恐怖文学、电子游戏等领域已然成为统治性的“显性美学”,然而我们却始终不能像提到超现实主义时那样,随意聊起布列东、达利、基里柯等如雷贯耳的名字,也几乎不能以书名号的形式来指代某一件具体作品。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当代美学研究中“本体论”流散的问题:具体的,成型的,完整的,形成完善的观看系统的,能将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文本,读者,作者,世界)明确地纳入到研究对象范畴的艺术作品,在如今这个以赛博数码为存在形式和载体的时代已经不合时宜。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波德莱尔所谓“稍纵即逝”的现代艺术,更是流散的,无法被定义和归纳的“非作品”性的艺术。“核类美学”的呈现形式都很难被改造成归类在文件夹里的单个文件,甚至它的前辈“蒸汽波”音乐都至少能以单曲的形式在音乐播放软件里映证自己。
以“怪核”为代表,早期的“核类美学”作品,甚至是以电脑病毒的形象出现在赛博世界中的。当用户打开这“无意义”的视频,只得到一些模糊的视觉印象和诡异的情绪的时候,自然会质疑此类视频存在的意义,甚至因为其劣质粗糙的编辑,开始怀疑这是一个卑劣的玩笑,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邮箱收到了垃圾邮件,怀疑这是不是一种散播恐惧的电脑病毒——这种被强加的“反讽”性,反而促使了“怪核”类视频的病毒式传播,本身“无意义”更是意味着“对不可知的难以把握”,人们总是会对“意义”的存在怀抱无限的期待。而“梦核”的多次元共生的大规模崛起,更是与TikTok的流行撇不开关系:刷TikTok本身的“无意义”与“核类美学”的虚无指向性达到先验的统一,在一个毋需答案的赛博环境里,给出答案反而是无趣的,是无法激发“惊奇”的,而情绪的抒发、视觉的印象和情感的共鸣,作为形式就成为内容,填补了一切文本“意义”所放弃的空间。在每一样作品被观众所凝视的时间都很难超过10秒的当代,“核类美学”提供了一种超越线性时间的感知方式:如空气,如光线,如普罗蒂诺笔下的上帝一般的,光速流淌开来,散溢进我们灵魂深处的氛围与感知,是本雅明以为早已消逝的,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光晕”(Aura)。
另一方面,“核类美学”的非作品性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作者的退场,和更加大众化的,群体性的,赛博形式的“作者”以更具有力量的集体主义形象的登场。这些图片和视频的作者并不可考,哪怕留下了网名,大都也不过是一些字母和数字的混合,也不会有任何观众在意他们本人,面目模糊的“怪核”创作者们更是宁愿躲进“阈限空间”也不愿意抛头露面成为被人关注的vtuber;但是,谁又能忽视这些无名的群体性作者的力量呢?在4chan论坛的网友闲聊中诞生的“后室空间”概念,迅速成为网友接力、涉猎全球的大规模赛博集体性创作,据不完全统计,如今的“后室空间”已经是一个拥有八层、数十万平方公里大小的“平行宇宙”,网友们不仅是要在这个世界里添加他们心目中“怪核”的“阈限空间”,更是要在这样一个宇宙中做解谜游戏乃至讲述自己的故事。
“后室空间”的起源现在看来几无特殊之处,仅仅是一张带有诡异色彩的黄色房间图片,其后续的群体性创作也时常被拿来当作“网友闲着无事可做”的例证,然而难道不就是这种对“无意义”的集体渴求心理,以及对完整性的放弃从而获取的高度参与性,促使“核类美学”更多以一种“氛围”而非“作品”的新形式存在于赛博世界中吗?从未来复古主义到蒸汽波,从Y2K千禧美学到“怪核”、“梦核”乃至“后室空间”,赛博世界流行亚文化的存在形式越发有“从重变轻”的趋势,从厚重的建筑、文学、电影到更加贴合生活的时尚、音乐范畴,直至彻底化作赛博世界里流溢飘散的“幽灵”,以“氛围”和“集体情绪”的形式时刻提醒我们它们的存在——
在理论上我们都不确定它们能否被算作“存在”,但我们却如同神学家一般笃定地相信它们存在:一如圣人看到了神迹,我们早已对“梦核”心醉神迷。
“中式恐怖”的本土化和当代流行文化的幽灵学
值得指出的是,以youtube病毒视频和TikTok短视频为载体进行传播的“梦核/怪核”,因其传播场域的限制性,本来很难在中文互联网世界掀起波澜——实际上,“核类美学”背后高度资本主义化时代的“城市病”特征,也并非国内文化界的主流。然而,借助大量的恐怖题材动漫和恐怖游戏的传播,“梦核/怪核”中对童年记忆追寻准确戳中了Y2K一代人的集体心理,而“核类美学”中独特的“阈限空间”概念也在各种中式的、国人生活的日常场景中得到呼应,“核类美学”借助“中式恐怖”近乎做到了最好的本土化,同时运用更加作品化的载体形式,在一个尚且需要传统的本体论对象的艺术接受环境中,达到了更好的传播和呈现效果。
从表意的含蓄和对“氛围”的重视来看,“怪核/梦核”美学是天然贴合“中式恐怖”含蓄绵长、具备历史文化厚重性、对个体采取心灵压制而非物理压制的基本特征的。如果说早期的“中式恐怖”作品,还集中于将传统中腐朽的封建文化形式与“吃人”的封建礼教相结合,试图更多地通过具体的“民俗”展示来突出压抑恐怖氛围的话,“核类美学”对“中式恐怖”的最大影响,即在于将恐怖故事的发生舞台从“过去”拉到了“当代”——不再需要面目阴沉的塑像,插在米饭上的筷子,诡异的锣鼓和红嫁衣,仅仅是一代青年人成长于兹的学校、幼儿园、交通站、游泳池、舞蹈房、文化宫等“生活场景”,就足以用童年阴影作为叙事桥梁来塑造场景的“心灵恐怖”;在不少“中式恐怖”游戏中,主角童年成长的重要环境,被用来负责“梦核/伤核”中惯用的甜美记忆场景,而这些场景的“阈限空间”化,指向的是童年甜美时光和天真纯洁心境的不复再得。“核类美学”将“中式恐怖”进一步扩展到普通人的心灵暗处:轰轰烈烈的有关反抗封建传统的生死故事可能都有些过度了,仅仅是我们的“成长”本身,我们童年所受到的私人创伤,乃至我们对于“大人世界”的迷惑和不解,都足以化作点燃我们灵魂中把我们禁锢入潜意识“Limbo”的地狱之火——
一百多年前,“克苏鲁之父”洛夫克拉夫特指出最高级的“心灵恐怖”,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怖”,而在“核类美学”的影响之下,中文语境下的我们对未知的恐惧,也正是对未来的“成长”的恐惧:对于Y2K一代来说最大的恐惧即在于,一个勉强美好的童年过后,我们都必须要以更加严酷的方式长大。
此时,哪怕在外人看来再“小题大做”,看来再“矫情没有出息”,我们还能够否认“梦核/怪核”美学背后如此普遍和强大的现实主义根基吗?当未来不再成为一种期待而成为一种恐惧,当我们的文化和美学都时刻选择一种哀悼与怀念的姿态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再次提及德里达在《Spectres de Marx》中对看似告别变革的21世纪的“幽灵学”担忧:所有的精神文化创作最终都将指向一个不可说的幽灵,这个幽灵无处不在地飘荡,成为屋子里的大象,是“深度探讨”必须涉及却又必须躲开的禁脔,整个21世纪的思想文化艺术,都将在这个“幽灵”的凝视下踌躇前行。
同时,我们还要提及文化理论家马克·费舍尔更具备明确批判性的“流行文化幽灵学”(Hauntology):因为我们看不见未来,所以我们流行文化中的“未来”也开始被取消了;2010年代的“蒸汽波”,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能发生的赛博未来的悲悼;2020年代的“梦核/怪核”,则就是21世纪初Y2K一代对短暂而美好的童年生活,对和平昌明、个体得以肆意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的追忆;那么宛若一种“中式”的“心灵恐怖”是,2030年代的我们将面对什么样的赛博文化潮流呢?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拿来追忆和悲悼呢?我们的流行文化根本就不是新鲜的,而是一个个不死的幽灵,死去的从来不曾死去,而是永恒缠绕在下一个世代,以怀念和悲悼作为底色来提醒人们美好时光的不复再得。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对幽灵的呼唤和回声之中取消了对未来的期待,改换为对当下的迟滞和对未来的恐惧,将自我沉溺在永远不做出选择、因此也不存在未来的“阈限空间”:我们为什么要做出选择?我们为什么要向前走?如果这盘桓在赛博世界中的流行文化幽灵时刻在提醒我们,未来是值得恐惧的,而要破除这种恐惧就需要解开幽灵的真面目,偏偏我们的上一辈、上上一辈早就告诫我们要对这个始终存在、始终飘荡的幽灵敬而远之?其实,费舍尔的流行文化幽灵学无非是德里达的幽灵学的幽灵,这整篇文章都仿佛在幽灵般地期待一种没有物质基础的纯粹赛博力量——在那个真正的幽灵揭开面纱之前,我们怎么能够奢望流行文化作为“独苗”或“破局力量”,率先摆脱这不断下坠的黑洞尽头呢?
重复:你要上去吗?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